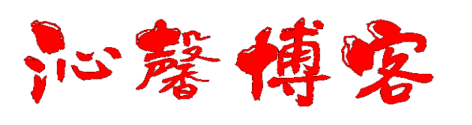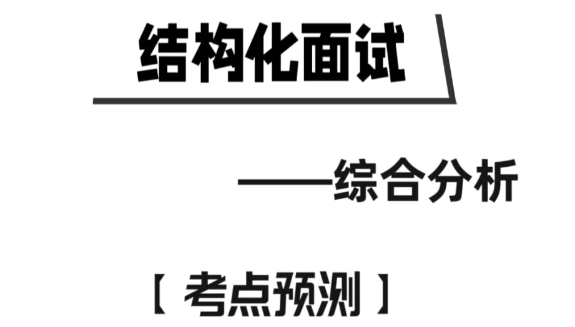酒醒何处觅归途
窗外的梧桐叶被夜风卷得沙沙作响,我蜷缩在教室最后一排,盯着抽屉里那瓶二锅头,额头不断沁出冷汗。三天前那场生日宴的荒唐场景,此刻依然像浸透酒精的棉絮般堵在胸腔里。
那日恰逢张同学十八岁成人礼,六个男生挤在KTV包厢里,用塑料杯斟满啤酒。头顶的霓虹灯将"禁止饮酒"的警示牌照得忽明忽暗,可当有人掀开整箱青岛啤酒时,欢呼声瞬间淹没了理智。
我清晰记得第三杯下肚时喉头的灼烧感,就像吞了团跳动的火焰,烧得人天旋地转。有人开始用奶油抹人脸,有人抱着话筒嘶吼,直到隔壁包厢客人报警,我们被警察带出时,走廊里碎玻璃正折射着凌晨三点的月光。
这让我想起去年校运会的糗事。田径队李学长赛前偷偷灌下半瓶白酒,四百米决赛时竟跑错方向,在全场哄笑中踉跄着栽进沙坑。那块本该挂在他胸前的金牌,最终成了教导处通报批评里的黑色注脚。更荒唐的是前年寒假,小区保安老周值班时偷喝药酒,醉眼朦胧中将归家业主当成劫匪,防暴叉直戳得人家羽绒服鸭绒漫天飞散。
酒精编织的荒诞故事里,最令我震撼的却是父亲同事王叔叔的遭遇。那个总把"酒品见人品"挂嘴边的业务经理,在年终答谢宴上硬生生灌下八两茅台。当他摇晃着推开酒店旋转门,栽倒时后脑勺撞击的大理石地面,至今留着洗不净的暗红色痕迹。ICU里昏迷的十三天,毁掉的不仅是他的职业生涯,更让读初三的女儿在高考前被迫辍学打工。
此刻教导主任的脚步声由远及近,我慌忙把酒瓶塞进书包深处。金属瓶身贴着掌心传来寒意,突然想起古籍里"酒是穿肠毒药"的箴言。那些被乙醇麻痹的神经,那些在推杯换盏间消散的时光,那些因醉酒失控造成的永久创伤,此刻都化作实体化的重压,沉甸甸地坠在胃里。
走廊尽头飘来桂花香,那是保洁阿姨在冲洗昨夜呕吐物。我摸出手机删掉所有酒水代购群,将存了半年的买酒基金全部转给山区助学项目。当夕阳把检讨书上的泪痕映成琥珀色时,我终于懂得:真正的成年礼不是酒精考验的虚妄勇气,而是保持清醒的智慧和担当。